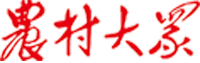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连载(22) | “岗姆冲”真的“冲”了出去
2025-01-16 10:08:35 来源:大众报业·农村大众客户端

第七章 回藏·还是那个透明的他
为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繁荣昌盛,我愿做雪山上的一盏明灯,把祖国的边疆西藏照亮。
1 . 这是孔书记给出的一道“岗姆冲”试题,看我能不能解开。
我一直觉得孔书记没有离开,一直还在岗巴,可他回山东了,我送的他。走在街上,我觉得前面那个个高肩宽的人是他,他在大步往前走,还不时回头看我;我来到县委办公室,觉得孔书记就在隔壁,过一会儿会过来叫我下乡;我踱步走到他住过的宿舍门口,期待着他推门出来,喊一声“阿旺”,再拍拍我的肩膀。我知道孔书记最爱穿灰色中山装,我也做了一件天天穿在身上……这就是念想吧,打从心里敬佩一个人,就会不由自主地学着那个人的样子做。
我们通过书信联系,鸿雁传书是件快乐的事情,仿佛在与他面对面聊天,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他以后,就像学生交了作业,等待老师批改打分,也像跟好朋友打乒乓球,小球在朋友之间来回飞转,球就是一封封的信、一份份的牵挂。我很怀念和孔书记之间写信、收信和读信的日子。
我写信说,县里安排我当了食堂管理员。他回信说,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管好了食堂,等于为岗巴建设做贡献。我说,县里又安排我当了文书,我应该怎样才能写好材料呢?他说,写文章的技巧无非是起承转合,但要想写出好文章还得走出去,好文章不只在办公桌上,在青稞田里,在牛群羊群里,在农牧民的锅碗瓢盆里。
快过年了,他给我寄了一幅他自己画的飞鹰图,图上还题了王维的名句“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”。他在信中说,这是对我的新年寄语,看事情要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,干起工作来要像冰雪消融后飞驰的快马。我把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,抬眼就能看到,每天都在找鹰和马的感觉。我觉得孔书记把情感都融进了笔墨里。他知道我爱写写画画,还建议我也画画,可我没坚持下来。
有一天我写信告诉他,全县的公社已恢复了乡制,我已申请到贡巴楼乡工作了,去磨一磨、练一练。他回信鼓励我大胆干,信中还提及那次调研时在门德村看到的卡垫。卡垫是岗巴一宝,如果以后能做成产业,就能撬动经济发展,也会成为岗巴的经济支柱,最终受益的是这片土地上辈辈受穷的老百姓们。
我记得3年前那次调研时,我和孔书记来到贡巴楼公社的门德村,刚进村就听到一曲婚礼上的迎宾歌:
“我已铺好雪域藏乡的四方羊毛毯,那上面铺好了卫藏花穗齐全的毛氆氇,最上面铺好了带穗的锦缎毯,毡毯上撒满了青稞、羊毛和柏叶,请送亲的客人高高兴兴下马进家门……”

婚礼上,岗巴的藏族男女会穿上最鲜亮的服饰。
我们赶过去看,见新娘缓缓下车,踩踏着图腾布包(上面是青稞,下面是茶叶);新郎给新娘用柏树枝蘸了水和牛奶抛洒,而后同坐在卡垫上接受大家的祝福和哈达。
婚礼上的摆设色彩艳丽,五颜六色的卡垫吸引了孔书记。他问生产队长平措卡垫是哪里来的。平措自豪地说,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做卡垫,主要是自家用,逢年过节相互赠送,结婚生子当贺礼。这里的卡垫也叫“岗姆冲”,意思是岗巴卡垫,是西藏民间最早的卡垫。

岗巴藏族同胞的婚礼。
这次孔书记的来信又提到卡垫,不由让我茅塞顿开,这是孔书记给我出的一道“岗姆冲”试题,看我能不能解开。我想,自己身为贡巴楼乡的副乡长,分管乡镇企业,若在门德村成立一个卡垫厂,把各家各户的卡垫集中起来,捆绑在一起推销,让“岗姆冲”火起来,这不就是“岗姆冲”试题的答案吗?可是,这道题答不好或答错了,就会劳民伤财。
孔书记在信里跟我讲,要学学陈云同志,陈云提倡“踱方步”,意思是说不要整天陷在事务堆里,要拿出时间来思考一些大事。陈云还常讲“瓜皮帽,水烟袋”,是指在旧社会的商店中,有一种人,头戴瓜皮帽,手拿水烟袋,他们不站在柜台前卖货,而是在后面观察,专门考虑店里缺什么货、什么时候应该进什么货这类大问题。我渐有所悟。
琢磨再三,我问自己,若是孔书记还在岗巴,他会怎么干?他会坐在桌前眯着眼想,或者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方步。按他的行事风格,他会先去摸底,搞清楚“是什么”,再定“怎么干”。
“是什么”呢?我住进了门德村,过去的生产队长平措是现在的村主任,他领着我挨家挨户了解情况,为卡垫“把脉”。卡垫,是藏族家庭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,是以羊毛为原料织造成的小型藏毯,与波斯地毯、土耳其地毯并称为世界“三大名毯”。门德村做卡垫已有近千年的历史,所用的原料是岗巴羊羊毛,羊毛柔细,这是当地卡垫好于西藏其他地区卡垫的“秘诀”。另外,这里出产的卡垫图案丰富,有二龙戏珠、彩云飞龙、青龙彩凤、花鸟等,单独纹样还有龙、凤、仙鹤、鹿、宝马、蝙蝠、蝴蝶、云纹、海水纹、宝相花、牡丹、兰花、梅花、竹、山水等,小小的门德村简直是一个“卡垫窝”,一个色彩缤纷的“卡垫世界”。

岗巴卡垫。
门德村里的编织“状元”叫尼玛嘎姆,20多岁,与许多藏族姑娘一样, 她有清澈明亮的眼睛和甜甜的笑容。她说,手艺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,她的阿妈从小就教她织造卡垫,十几岁已是炉火纯青,无论是一朵花、一只鸟, 还是传统图案,她看一眼就能印在脑子里,并通过织机和巧手“复制”到卡垫上。
我坐在尼玛嘎姆的身旁,看她织造卡垫。只见她用古老的“穿杆打结”法编织,脚踩动踏板带动桄综,经过经纬交织、上下交错的穿线方法,卡垫上自然形成了纵横条纹,看上去错落有致、层次分明。再看卡垫背面的疙瘩造型也别具一格,粗犷古朴中透出自然和谐之美。我真的被她这双巧手所折服。她拾个树棍儿或瓦片儿,在地上、石头上、墙壁上,甚至在腿上画。她说,这叫谋着,心里谋着个啥就能织出来个啥样儿。
平措说,前几天从北京来旅游的一位美术师要看村里最好的卡垫,当他见到了尼玛嘎姆织造的花草图案的长毛卡垫后,连声说好,还说藏地其他地方的卡垫图案有的古板,有的过分夸张渲染,只有这里的卡垫图案分寸把握得最好,把飞鸟花草都织“活”了。
尼玛嘎姆说,卡垫看起来鲜活灵动是因为她把祖传的图案改了,比如把静止的花改成风中的花,再加上蜜蜂、蝴蝶,画面就“活”了。还有,好图案来自多个方面,岗巴羊毛好但油脂多,要在水中捶砸挤压,用碱水洗净;再用弓弦、皮条、细竹弹毛;还要用本地的植物、矿物质、色土上色染毛,染出深蓝、浅蓝、黄、浅黄、橘黄等十几种颜色,颜色越多,搭配得越丰富。编织时手中的线还要一丝不乱。
“卡垫窝”让我心里有了“底气”,接下来就是琢磨“怎么干”。
我和平措商量要成立家卡垫厂,村里所有的卡垫手艺人都是厂里的工人。
卡垫厂统一收购大家编织的卡垫后销售,利润交给集体。平措高兴得合不拢嘴,当天就召开群众大会通知这件事。我看到开会前,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聚到村里的广场上,他们拿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“显摆”。这个的“二龙戏珠”用线匀称,那个的“彩云飞龙”鲜艳夺目;这个的“花鸟”编得有些拥挤,那个的“蝴蝶”用色不准。大家品头论足,有时争得面红耳赤。最后,大家请尼玛嘎姆评判。这位姑娘真是干织造的天才,色、线、层次说得头头是道,还能说出手艺人在编织的过程中因速度快慢造成的视觉影响,直说得大家口服心服,都叫她“巧手嘎姆”。

岗巴卡垫。
这个时候平措对大家说,门德村是“卡垫窝”,可这些年来很少有卡垫买卖,咱们让手艺变钱,成立一个卡垫厂,收购大家的卡垫,让“巧手嘎姆”当质量检验员,以质论价。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,唱起了歌,跳起了舞。尼玛嘎姆不光是“巧手嘎姆”,她的歌如溪流淙淙,舞若春风杨柳,喝彩声四起。平措拿来纸笔,我分别用藏文和汉文写下了“门德卡垫厂”两行大字。我这是第一次写厂名,汉文的“厂”字用的是繁体字。
热闹过后,我们从县里办了营业执照,但启动资金成了难题。我想,若是孔书记在这里会怎么办呢?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钱拿出来。对,我也要这么做!我马上到银行取出所有的积蓄拿到卡垫厂,平措过意不去,也把自家的钱拿来了,“巧手嘎姆”精选了十几个精品卡垫免费送到厂里当样品。
万事开头难,卡垫往哪里卖?怎么推销?若是孔书记,他又会怎么办?他会带着我马不停蹄地走出去跑销路。对,我也这么做。我和平措带着干粮、拿着卡垫样品跑到了日喀则。
一开始,我们在街上举着卡垫求买家,问的多买的少。后来,我们哪里人多往哪里去,这叫蹭“人气”,一天能卖上七八个。那天,我们在扎什伦布寺大门口遇到一位四川游客,他看到卡垫爱不释手。当知道这是岗巴羊毛织出的“岗姆冲”时,他跟着我们来到门德村,看到“巧手嘎姆”的编织技艺赞不绝口,一下子订购了100个,总货款5万元,卡垫厂赚到了“第一桶金”。
我和平措趁热打铁,又跑到日喀则的工艺品经销店,签了几十家代销合同,一年卖了几百个卡垫。
年底“算盘响”,卡垫厂收入30万元,利润五六万。门德村的人高兴了,集体经济有“根”了,村里的贫困户从此可以吃得饱、穿得暖了。
几年之后,卡垫厂越做越大,名声越来越响。过年了,我又用墨把“门德卡垫厂”的牌子描了一遍,显得跟新的一样。这里成了岗巴县的卡垫销售集散地,全国各地的客户纷纷来厂订购。随之而来的是村里修路,村民盖房……“岗姆冲”真的“冲”了出去。这道“岗姆冲”的题我答对了。
1988年10月的一天,我给孔书记写了一封长信,把办厂子的过程说了一遍。他的回信很简短:“阿旺,祝贺你,‘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’是也。我将近日带领15名山东援藏干部去拉萨,面叙。”信中附有他写的一首长诗,题目是《第二次出征西藏》:
我不喜欢孤独的吟唱,
我不喜欢哀婉的忧伤,
我喜欢淋漓的欢乐,
我喜欢火热的生活,
我喜欢国土的广阔。
今天,接到命令 :
奔赴西藏,第二次奔赴西藏,
我又陷入遥远的回忆——
想那片草原,
想那片有蓝天白云的高原,
想那片酥油茶飘香的高原,
想那片流淌草原牧歌的高原,
想那片剽悍雄性的高原,
想那片佩藏刀饮大碗青稞酒的高原,
想那片雄伟高大的天然屏障,
过去了,又走回来——
离开故乡,离开那片养我育我的平原,
我不敢再想白发老母倚门望我归家,
我怕太阳下山之后,
大野里传来母亲的呼唤,
唤我,唤我,归家;
我怕那门前的酸枣树开花又结籽,
红透了以后,攥在母亲的手掌之中,
等我,等我,等我回家——
谁都有儿女情长,
羊羔跪乳,燕子衔食,
我知道男儿应该远行,
离家之前,我只想说——
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养人。
我知道出征的路程和分量,
我知道荣誉和牺牲、胜利和艰难,
绝不会单一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,
我要用妈妈的教诲、妻子的期待、朋友的支持,
来激励我勇敢顽强地站立在祖国的高原——西藏。
为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繁荣昌盛,
我愿做雪山上的一盏明灯,
把祖国的边疆西藏照亮。
我让“巧手嘎姆”编织了一个“梅”的卡垫。朵朵梅花,怒放在天地之间,探霜傲雪,剪雪裁冰,一身傲骨,坚忍不拔,我要把它送给孔书记。
我等着又回雪域高原的孔书记。
未完待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