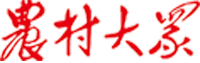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连载(19)|他叮嘱我,到村里不要叫他的职务,要叫曼巴(医生)
2025-01-13 10:01:00 来源:大众报业·农村大众客户端

第六章 情浓·他把老百姓捧在心上
孔书记背上了背包,像3年前来的时候一样,只是脖子上多了层层叠叠的哈达,俨如盛开的雪莲。
1 . 他还拍拍药箱叮嘱我,到村里不要叫他的职务,要叫曼巴( 医生)。
孔书记的朋友多,有老战友、老同事,还有许多年轻人。他订的报纸和收到的信件也多,一摞一摞的我都替他发愁,他怎么看啊。有一次,他悄悄地跟我说,四川和安徽农村已经开始搞“包产到户”的试点了。他朋友在信中告诉他,了解到老家山东菏泽地委在搞“菏泽八条”,核心是生产队包产到组,有的地方包产到户。主持这个事儿的是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。这位书记还推出了农村屠宰“两把刀”政策:“一把刀”留给公社屠宰站,按照规定杀猪;另“一把刀”给自己养猪的农民,经过市管所批准之后,他们杀的猪可以上市。这“两把刀”一经推出,整个市场大变样。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惊讶,也很新鲜。
大概是27年后的2008年,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了周振兴书记的故事——《地委书记的耳光》,这一下子让我想起孔书记当年说过的周振兴。文章是这样写的:
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仲春时节,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革命老区曹县韩集乡,看望杨得志将军当年的老房东、老共产党员伊巧云老人。随同的有曹县县委书记、武装部部长等人。到韩集后,周振兴书记没在乡镇和村委会停留,直奔伊巧云老人家中。
老人已重病在身,周振兴握住老人枯瘦的手,问老人还有什么要求, 伊老人犹豫了一下,说:“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。”说完,老人又后悔了,用另一只手拍打着周振兴的手背:“也就是这么一想,周书记别当事。”
历来以雷厉风行、低调工作的作风著称的周振兴,一下子泪流满面。他双手握住老人的双手:“怪我,怪我们啊,老人家,对不起您。”他抹了一把脸,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钱,递到赶来的公社书记手中,其他领导纷纷掏自己的衣袋,被周书记一把按住了。
毋庸言说,老人当天就吃上了肥中带瘦的肉。

1978 年1月,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调研听取群众意见。
随后,周书记回到县城参加了县委的一个汇报会。会上他眼含热泪地讲了一段话——
“伊巧云老人今年83岁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她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。在抗战堡垒红山村,做杨得志将军的房东时,为接待来往的将士,她曾一天做过九顿饭,为了让将士们吃饱吃好,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。现在,在我们领导下,生重病了,竟吃不上一口肥中带瘦的肉。同志们,我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?”
说着,周书记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,说:“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,还叫脸吗?”
这一记耳光打得是那样清脆,话说得那样沉重。坐在他身旁的县委书记一下俯在桌上,低声哭出声来。“周书记,该打的是我,是我,请地委处理我。”一时间,所有与会人员都低下了头,收起了原先准备好的各自工作成绩的汇报稿。
读了这篇文章后,我忍不住落了泪。这是一位好书记,孔书记也是,是一位牵挂着百姓冷暖的好书记。
我们这里搞包干到户,是1981年的事。先是1980年底,岗巴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。会上,县委书记张华宣读了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文件,文件中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干到户、包产到户,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。
我记得,孔书记那天宣读了日喀则地委《关于“双包”到户责任制中处理若干具体问题的参考意见(讨论稿)》。会议明确提出以“两个长期不变”(土地归户、自主经营长期不变,牲畜归户、私有私养长期不变)为主要内容的农牧区改革政策。
会议内容引起了轩然大波,这些年来,一直强调“一大二公”,怎么说分就分呢?说真话,这个弯儿拐得有点儿大,我也想不通。
会后各个公社进行讨论,讨论的结果几天后上报到县委办公室。汇总意见后发现,各公社都没有行动。那天张华与孔书记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个上午,上级指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,怎么解开思想疙瘩是当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。孔书记想到了调查研究这个法宝,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,更没有决策权。
孔书记主动请缨去各个公社调研,摸清农牧民的现状和真实想法,然后选一个公社作为试点,有了成功经验后再在全县推开。
孔书记定的调研计划是,进村入户,听真话,看实情。他还拍拍药箱叮嘱我,到村里不要叫他的职务,要叫曼巴(医生)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们从岗巴出发骑马前往直克公社。直克在岗巴的西北,不足千人,以放牧为主,土地少。我们到达海拔5000米的吉荣村时已是下午,看到田里的草比青稞苗还高,孔书记的脸阴得吓人。我们在村边找个避风处吃了点儿糌粑,喝了几口水壶里的凉水,算是吃了午餐。
进村后,推开村头一家的篱笆院门,见院子很大,院角有个羊圈,两间土坯房,墙壁因年久失修“龇牙咧嘴”的。屋门大敞着,屋内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,屋里有破桌一张,桌上供着一个石雕佛像,床板上有一张席和一床破棉被。家里没人,我们在院子里等。大约半小时后,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赶着十几只羊,“喀喀喀”弓着腰、有气无力地走进来。孔书记问:“天还早就把羊收了?”中年男子说:“咳得不行了,头还疼。”他说着把羊赶到羊圈里,鞭子一扔,就倒在了屋里的床板上哼哼起来。
孔书记给他试了试体温,又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后背说,发烧38.5度,肺有杂音,估计是流行性感冒,又从药箱里拿出几片治疗感冒的药让他服下,还在他的几个穴位上扎了银针。
过了一会儿,中年男子身上觉得轻快了,坐起身来,说,你这曼巴来得正好,村里不少人都中了邪气,得了这种怪病,头痛得要裂开,人像掉了魂一样,今天还有人到五六里外的寺庙求佛去了。
孔书记一惊,问,生产队长呢?中年男子说,队长去走亲戚了,他叫桑拉,是生产队副队长。孔书记说,这不是中了什么邪,是流行性感冒,传染快,快去告诉村民们,到这里来给他们治疗。
桑拉趿拉着鞋到街上喊“曼巴来了,快来治邪病了”,不一会来了十几个人,孔书记忙着给他们扎针、分药。
天黑时,十几个到寺庙求佛的人回了村,听说来了曼巴,都忽拉拉来到了院子里。孔书记给他们一个个治疗着,尽管春寒料峭,但他脸上还冒着豆粒大的汗珠。晚上10点多钟治疗完最后一个病号,他长舒一口气,正要喝口水歇一会儿,一个少年跑来说,他奶奶的腿不好,走不了路,能不能请曼巴到家里给奶奶看看病。孔书记二话没说,背着药箱赶往他家。
村里还有五六个因腿疾、腰疾不能下地的,孔书记便一家一家地上门去治疗,半夜才回到桑拉家。桑拉早已睡下了,显然是因为感冒药里有镇定成分,叫了几声也没有回应。我只好从羊圈边找了块草苫子铺在屋里。孔书记可能是太累了,往苫子上一躺就打起了呼噜。我不敢再打扰他,悄悄地躺在他身边。
第二天一早我被桑拉推醒,让我帮他到羊圈里抓羊。我们把一只羊拖到院子中间,只见他从腰里拔出一把铜柄的藏刀,一刀刺在羊脖子上,羊血汩汩流到一个大盆里。接着,他剥了羊皮又开膛,再分割了投到屋门前的铁锅里。短短的十几分钟,他已点着牛粪煮上了羊肉。
他看到我们吃惊的眼神,说,杀只羊感谢曼巴,给村里那么多人治病。

孔繁森工作之余为农牧民看病。
孔书记被他的热情感动了,悄悄把20元钱压在桌上的佛像下面,并与他聊村里的情况。我看到孔书记在笔记本上写道:直克公社吉荣村,土地300亩,人口198人、35户,牲畜(集体有牦牛10头、羊105只,农户有牦牛50头、羊200只),全村人生活用肉能够满足,青稞年产量不足5000斤,平均每人25斤左右。
孔书记问桑拉:“为什么青稞亩产不足20斤?”
桑拉说,他们村过去是游牧生活的,哪里有草往哪儿去,几十年前才在这里定居。村里过去一棵青稞也不种,这些年才开始种。地是村里集体开垦的,初夏的时候组织一些村民到好一些的地块撒种,苗和草一块长,到秋天就拿着镰刀去拨开草找青稞收割。赶上大旱,连种子都收不回来,大家就更不愿意种了,有些地到现在还一直荒着呢。
孔书记说:“怪不得田里的青稞没有草高。你们光吃肉不吃糌粑吗?”
桑拉说:“要么先卖了羊再买青稞,要么到集市上或邻村直接用羊换糌粑。”孔书记叹口气:“你们不是土地少,而是让地荒着,真让人心疼呀。如果把地分到各家各户,村里人还会不管不问吗?”
“过日子一分一厘不嫌少,地成了自家的就会上心了,只要用心用力,老冰坨子也能融化,何况是种地呢?”
一大盆热腾腾的羊肉端上桌,“羊吃胸叉,牛吃肋巴”,桑拉把一大块胸叉骨拿给孔书记,催着他趁热吃。孔书记分了一半给我,边吃边重复着“只要用心用力,老冰坨子也能融化”。
之后的几天里,我们又去了这里的三个村调研,印象还是:贫穷、落后和懒惰。
来到孔玛公社时,山上的草长得明显好多了,郁郁葱葱铺满山顶。在一块向阳的山坡上,我们正要放马去吃草,眼前的牦牛群里两头牦牛忽然打起架来。牦牛忽而用强壮的脖子和肩膀互相推挤,忽而用锋利的牛角刺向对方,边打边发出响亮的吼声。这种场面生人是不敢靠近的,我们只好四下张望,寻找放牛的人。我和孔书记着急地大喊:“谁的牛群,快来看看!”却没有回音。
我们跑到山坳里,看到两个中年人把牛鞭扔到地上,正在玩骰子。孔书记说,你们的牛打起来了。他们玩儿得正起劲儿,没搭理我们。我又说,你们的牦牛打得浑身是血。其中一个人有些不耐烦地说:“打就打吧,死了做牛肉干吃。”
孔书记火了,大声呵斥道:“这是集体的牛,死了要负责任,现在你们马上去管管牛!”他们抬头看到了我肩上斜挎的枪和孔书记身上的药箱,觉得我们是“有来头”的人,马上挥着鞭子跑向牛群。
牛群安静了下来,孔书记的心却没有平静。他说:“这些人也是‘老冰坨子’。”
再往山下的村庄走,孔书记突然脚下一滑,摔倒在地上。我立即扶起他, 他拍拍裤子上的土说:“没摔着,没事,咱到那个村里转转看。”
我忽然发现他的蓝裤子后裆被石头划开了一条十几厘米的口子,里面的红秋裤露了出来 ,十分显眼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孔书记两手一摊说,没带替换的裤子,这可怎么办?
我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。我让他趴在一个土坡上,从药箱里拿出一块白胶布,撕成条,把他裤子上的口子给粘上了。接着,又拿出钢笔,给白胶布涂上蓝墨水。然后,我对孔书记说:“这下你尽管放心了,不会有什么破‘绽’了。”
孔书记用手摸摸粘合的口子,表扬我脑子转得快,还嘱咐我,以后在药箱里放一个针线包。他刚当兵的时候,新兵连给每个人都发一个针线包,衣服破了自己缝补,挺方便。
刚到村口,遇见一群牧归的羊,有几只调皮的羊跑到路边的青稞田里吃青苗。我们骑马过去阻止,见这片地里的青稞稀稀落落,特别是路边的青稞苗已被吃得所剩无几。
放牧的年轻人倒不高兴了,说:“这几只羊吃草没吃饱,让它吃几口苗没什么。”
孔书记说:“吃上一片青稞就是一家人的一顿饭,这怎么能行?”
牧羊人不服气地说:“队长说了,这片青稞可以让牛羊吃,青稞也是生产队的,牛羊也是生产队的,牛羊吃了苗长肉,大家再吃牛羊肉,这不是一个样儿吗?”
孔书记一听,急了,对牧羊人说:“去找你们的糊涂队长来。”牧羊人嬉皮笑脸地回答:“去吧,队长正在玩儿骰子呢。”
孔书记摇摇头,对我说: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。包干到户,就是自己咬自己的肉,心疼了,也就上心了。”
我们到了生产队办公室,果真,有几个人正在玩儿骰子。生产队长认出了在县里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文件的孔书记,立马笑脸相迎。孔书记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训斥,追问他“牛羊吃了苗长肉,大家再吃牛羊肉”的说法。队长低着头承认说过这话,他觉得村头那几亩青稞长得不好,进出村子的牛羊又乱啃,干脆改种土豆。
孔书记勃然大怒:“你这是在糟践粮食糟践地,你不配当这个队长!”
调研了30多天后回到岗巴,孔书记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,但药箱却空了。他打发我到县里买药,还列了个药品单子,可在钱包里只翻出来48块钱。他只好又给县医院的土登医生写了一封信,意思是如果药费不够,先记账,等8日发工资时一并结清。
我说:“孔书记,你每次买药都花五六十元,工资都搭进去了,自己连饭都吃不上了。”
他说:“这就叫好钢用在了刀刃上,你知道看到病人病情减轻了、好转了,心里是什么滋味吗?那真是打心里高兴呀。”
孔书记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一份《岗巴县包干到户的调研报告》,我当了第一读者。我看到,材料打破常规,在第一段写道:农牧民自留地里的青稞为什么比集体的青稞长得好?自家养的牛羊为什么比生产队里的牛羊健壮?通过这次对岗巴所有村庄的调研,得出的结论是,要快些实行包干到户,快些把农牧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岗巴不能再等了,老百姓不能再受穷了。
这份调研报告在县里反响强烈。很快,县委、县政府决定由孔书记牵头,将昌龙公社作为包干到户试点。
昌龙的“老冰坨子”能不能融化呢?
未完待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