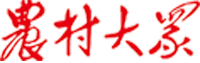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连载(12)|他笔挺地站立着,目视前方,与哨兵没有两样
2025-01-06 10:00:00 来源:大众报业·农村大众客户端

第三章 相融·绿叶对根的情意
孔书记对拉吉说:“阿佳拉(大姐),山上又险又冷,你身体不好,不要去了。”
没想到拉吉不同意,她说:“金珠玛米(拥有菩萨心肠的救苦救难的兵)在边境一线守护我们,挨冻受苦,我要去的。”
5 . 我跑到大门外,正要问值勤的岗哨,发现岗哨竟是他,他笔挺地站立着,目视前方……
快到藏历年,一大早我就给孔书记讲藏族人过藏历年的年俗。
岗巴人为了迎接藏历年,从藏历十二月初便开始准备供过年吃、穿、玩、用的东西。这时家家户户开始在水盆中浸泡青稞种子,培育青苗,藏历年初一那天,要将长了一两寸的青苗摆于佛龛茶几之上,预祝新年粮食丰收。藏历十二月中旬,家家户户准备酥油和白面,陆续炸“卡塞”(油果子),有耳朵状的“苦过”,有长条形的“那夏”,有大麻花似的“木东”,有圆盘状的“不鲁”,还有勺子形的“宾多”。
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晚是“古突夜”,类似于汉族人的除夕夜。晚饭前,要在打扫干净的灶房正中墙上,用干面粉画上“八吉祥徽”(有8种吉祥物的祥徽),在大门上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、永恒的“卍”符号(藏语称为“雍仲”,象征吉祥如意),有的人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点,表示人寿粮丰。晚饭各家都要吃“古突”(“古”即“九”,表示二十九日,“突”意为“面糊”)。“古突”里会包着多种东西,有石子、辣椒、木炭、羊毛等物。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团,预示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;吃到木炭预示心黑;吃到辣椒表示嘴如刀;吃到羊毛说明心肠软。吃到这些东西的人,都要即席吐出,这往往引起哄堂大笑,以助节日之兴。古突之夜,各家根据经济条件, 在佛像前摆好各种食品,准备好节日的新装。家庭主妇煮好“箐锅”( 放有红糖、碎奶渣、糌粑、人参果等的热青稞酒),初一早上天刚亮就送到家人面前,让他们喝。

岗巴县人民欢度藏历年。
大年初一,家庭主妇最先起床,洗漱完毕,到井里打上第一桶水,喂饱牲畜后回屋唤醒家人。全家人穿好新衣服后,按辈分排位坐定,长辈端来五谷斗,每人都先抓上几粒,向天上撒去表示祭神,接着依次抓一点儿送进自己的嘴里。这时,长辈依次向晚辈祝福“扎西德勒”,后辈回贺“顶多德瓦吐巴秀”。举行过新年仪式后,便吃青稞片、“突巴”(面糊)和酥油煮的人参果,互敬青稞酒。这一天,全家闭门欢聚。从初二开始亲戚好友之间互相拜年,持续3至5天。
新年里,孩子们燃放鞭炮,成年人喝青稞酒、酥油茶,互相祝福,尽情欢乐。城乡表演藏戏、跳锅庄和弦子舞。牧民们点燃熊熊篝火,通宵达旦地尽情歌舞。节日期间,民间还有角力、投掷、拔河、跑马射箭等一系列活动。我娓娓道来,孔书记的脸上却露出了难色。他说,过年热闹,可也是过关呀,过去欠租、负债的人必须在这时清偿债务,所以过年像过关一样。现在岗巴人的日子还不好过,又刚遭了雪灾,有的农牧民过年也像过关呢,我们还是准备走访走访贫困农牧民吧。
我提醒他,按规定你可以回聊城过年,走访的事有格热呢,你还是回趟家看看老母亲和孩子们吧。他说:“屁股还没坐热就往家里跑,不合适。再说,来来回回得一个月,回去又要醉氧,折腾不起,还是等明年吧。”我说:“你不想家吗?”他说:“人心都是肉长的,哪能不想,记得当兵的时候一到过年想家想得睡不着觉。”说到这里,他突然让我给县里写个申请,到查果拉哨所慰问部队的指战员。
昌龙之南是喜马拉雅山,喜马拉雅山第七峰是查果拉山,山上有个查果拉哨所。这个“世界屋脊”上最高的哨所,海拔5318米。有“查果拉查果拉, 伸手把天抓”的说法,“查果拉”的藏语意思是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,但这里几乎看不到一草一木,更不用说鲜花了。哨所驻地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,年平均气温在-10℃左右。盛夏时,这里的鸡蛋也会冻得梆硬,得用锤子砸开。查果拉常年风雪猛烈,五天就要换一面国旗。边防官兵担负着查果拉、控扬米和西西拉三大山口的巡逻任务,每个山口海拔都在5500米以上,途中要爬雪山、蹚冰河、越险滩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几天后,县里批准了孔书记带着电影放映队到查果拉哨所慰问的申请。格热、拉吉夫妇知道了,从家里装了两口袋糌粑也要与我们同行。孔书记对拉吉说:“阿佳拉(大姐),山上又险又冷,你身体不好,不要去了。”没想到拉吉不同意,她说:“金珠玛米(拥有菩萨心肠的救苦救难的兵)在边境一线守护我们,挨冻受苦,我要去的。”
慰问的马队出发了。望着眼前的雪山,孔书记说,1950年3月,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走过几千公里的路程,翻过十几座海拔 4500米以上的雪山,跨过几十条大小冰河,穿越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沼泽草原,终于到达了西藏。他们用汗水、鲜血乃至生命,修通了总长3400多公里的青藏、川藏两条公路,可以说,每一公里都有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。在大雪纷飞、寒风凛冽的野外,战士们磨秃了千万根钢钎和铁锹,手上常常裂开一道道血口,裂口在打钎炸石中出血、愈合又裂开。川藏公路修到通麦和鲁朗之间的帕隆时,有一个排在石崖上,用绳子吊起来打炮眼,“咣当”一声,绳子断了,整个排都掉到江水里被冲走了。后来的战士们提出震撼人心的口号:“让高山低头,叫河水让路。”前前后后,有3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长眠在这里……
1962年8月,一支身穿绿色军装、扛着红旗的队伍,迎着纷飞的大雪,沿着荒无人烟的山坡向查果拉山进发。凭着一颗红心、两口铁锅、三顶帐篷,第一批查果拉官兵就在这里安了家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查果拉哨所。
太阳西坠时,我们看到了冰峰之上赭黄色的哨楼和猎猎飘展的五星红旗,还有笔挺站立、手握钢枪的哨兵。墙上是“没有牺牲不得的己利,没有忍耐不住的寂苦,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”的标语。天上见不到一只飞鸟,周围雪山绵延,银装素裹,刺骨的寒风像刀子割着人的脸。
战士们列队迎候,像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。孔书记打了个标准的军礼后与战士们握手拥抱。进屋后,孔书记手捧战士们送来的酥油茶,听着战士们讲述哨所的故事。
一位年轻战士说,踏上查果拉山,首先面临的是高反,头痛腹胀腿软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每天还要从几里外背来冰块,融水做饭,气压低,沸点才60℃,没有高压锅,煮出的饭不是生就是煳。
一位老战士说,风大雪大,常年冰雪不化。我们之前住的是帐篷,睡的是地铺,吃的是夹生饭,喝的是冰化水。我们几年没有吃过一次新鲜蔬菜和水果,没有看过一场电影,没有洗过一次澡。由于天气太冷,很多人的腿都冻坏了,甚至有的战友不得不将冻坏的双腿锯掉……
有位战士骄傲地说,查果拉周围一片冰雪,没有可用的土,我们就到20多里以外的地方背土上山,打土坯建房屋,经过几个月的劳动,终于建造了简易的宿舍、食堂,还有一个篮球场。
…………
我看到格热双手合十,拉吉的眼角挂了泪水。
孔书记动情地说:“战友们,我也是名老兵,没有你们受的苦大,向你们学习!”
战士们说:“当兵守边防,天经地义,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“苦是苦了些,可心里舒坦呀,只要全国人民能安心搞建设,我们这点儿苦算啥?”
你一言我一语,有个战士竟说起了他们自己编的顺口溜:
天上无飞鸟,地上不长草;
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;
六月雪花飘,四季穿棉袄。
安家在雪山,脚踏云雾间;
沙石击面痛,风雪刺骨寒;
心为人民乐,愿与艰苦伴。
战士说罢,拉吉也唱起了《心中的歌儿献给解放军》。在我的记忆里,年近50岁的拉吉并不识字,但歌词记得那么准确。格热听着也随声唱了起来,孔书记和战士们也跟着唱了起来,独唱变成了合唱。
放电影的时候已是夜里10点多钟,先放的是《奇袭白虎团》,战士们看得如痴如醉。接着再放《白毛女》,当喜儿在风雪中唱着“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,雪花那个飘飘,年来到……”时,我看到许多战士流下了眼泪。
这时我忽然发现孔书记不见了,打了个激灵,哨所那边就是印度,万一出事了不得。我急忙屋里屋外地找,还是不见他。我跑到大门外,正要问值勤的岗哨,发现岗哨竟是他,他笔挺地站立着,目视前方,与哨兵没有两样,只是他那顶帽子上没有帽徽,眉毛和鼻孔周围已结了冰花。他冲我笑笑说:“我替小战士站岗,让他去看电影了。”
电影放完时,一个小战士被连长拉到门外的哨位前训斥:“你为什么脱离岗位?”孔书记马上给连长打了个敬礼说:“报告连长,责任全在我,我接的岗,我也是名老兵,也是名战士。”
连长苦笑着摇摇头,还了个军礼:“对不起,首长!”
我看到孔书记的手套都粘在了钢枪上,手脚都冻得不听使唤了,赶忙扶着他走进营房。
第二天,和查果拉告别的时候,突来一阵风雪,为我们一行的离别平添了一份悲壮。风雪中,孔书记和列队的指战员们逐个握手,面对战士们的军礼,他很自然地举手还礼。
“几年没有吃过一次新鲜蔬菜和水果”,那位战士的话让孔书记记在了心里,回昌龙后他连夜给妻子写信,说了查果拉哨所战士们的艰苦,要求多寄些干茄子、干豆角来。此后,每次寄来蔬菜,他就骑马去哨所送给战士们。有一次临别时,他提出要去看看那些牺牲战友的墓地。连长把他领到哨所边一个大雪堆旁,孔书记跪了下来……
回县城的路上,他写下了一首诗:
多少人民血,
换来边关宁。
思之立壮志,
虽苦有笑声。
未完待续……